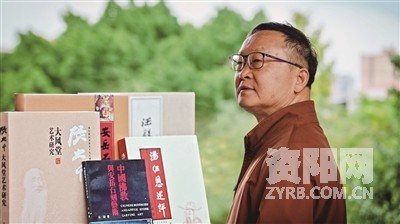
汪毅与他的部分著作。
□全媒体记者 钟雷 蒋婷婷
一片“石头的世界”,开启了一位知青与资阳安岳的深情守望。在乡野与石刻的偶遇,引发了一名文化工作者贯穿半生的文化苦旅。年过六旬,他将积累数十年的典藏和一批重要学术研究成果捐与安岳,以文化反哺润泽一方。今天的《天南海北资阳人》,走近一级文学创作(教授)、《四川省志》原副总编、文化学者汪毅,听他讲述他与安岳石刻的半世情缘。
石缘
一场美丽的相遇
1975年,汪毅以知识青年的身份,从重庆来到安岳县思贤镇插队落户。这个“走进来”的抉择,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
“当时我发现一些佛头被遗弃,比如被扔在苕沟、地沟里,无人问津。我就觉得,无论是从善心的角度,还是从艺术的角度,都应该把这些东西好好保护起来。尽管当时这些想法不是很系统,甚至是一种朦胧的状态。”劳作之余,当汪毅看到那些散落在乡间僻静处的佛头如同一颗颗蒙尘的明珠时,爱惜之情油然而生。这种朴素的责任感,成为他后来系统研究安岳石刻的最初火花。
1982年3月,已经在安岳县文化馆工作的汪毅迎来人生中的一次重要经历。“省、市(地区)组织文物普查,我们文化馆一个老同志就提供了一个线索,他说他的老家有一尊很大的卧佛,非常大。”汪毅回忆道,文物普查组在了解到相关情况后,随即到安岳进行实地考察,他也随队前往目的地八庙乡。当那尊巨大的卧佛在晨光中缓缓露出真容时,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现场所有人员都屏住了呼吸,震惊不已。
在返程路上,汪毅迫不及待地写下报道《安岳县发现罕见的盛唐时期卧佛和经文》。“1982年3月底,《四川日报》把这个报道发出来了。随后就如同核爆炸一样,引起了轰动,很长一段时间卧佛现场都是人山人海。”
求索
从安岳石刻到世界瑰宝
汪毅没有止步于一时轰动,接下来,他接连在海内外报刊发表了120多篇关于安岳石刻的研究性文章,出版了《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》和《安岳石刻艺术》专著,把安岳石刻首次推向国际学术论坛,创造了宣传安岳石刻的若干个“第一”。1986年,汪毅赴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深造,这期间他不仅没有把安岳石刻研究放在一边,反而对其有了更加系统的研究。他说:“同学们入学时都带了些各地的土特产来分享,大家都说我带得最多,但让大家都意想不到的是我把行李打开一看——一大摞清代的《安岳县志》。”汪毅表示,正是借助对这些县志等资料的研究,进一步深化了他对安岳石刻的认知。
“大家都说紫竹观音美,但美在哪里,怎么构成的呢?比如安岳石刻的飞天美,还有形态美,甚至大美、壮美、悲剧美。我从美学角度来做一些思考,就拓展了石窟艺术研究的领域。”与其他研究者不同,汪毅是从文化研究而非文物工作的角度切入,让安岳石刻的研究有了新的维度。经过多年的沉淀与积累,他率先提出并阐释了安岳石刻“承上启下”“古多精美特”“安岳石刻学”等重要学术命题,并从美学视角观照安岳石刻。
归来
万件珍藏皆是深情
43年过去,汪毅已然成为安岳石刻研究领域的重要奠基者之一,他为安岳石刻研究及其在国际学术界的推广作出了突出贡献。不过,长期以来,在他心里,“安岳石刻学”还缺少一个贯穿岁月的具体承载。
“我是觉得,从哪里来,就应该回到哪里去,因此我就应该把这些资料回馈给安岳。”2020年世界读书日当天,年近65岁的汪毅回到自己文化苦旅开始的地方——安岳县,开启了一场“文化反哺”行动,他将积累半生的安岳石刻研究学术成果、重要典藏及书画作品等捐给安岳县图书馆,各种资料、物品的总重量达3.5吨。“从2020年开始,我每年都持续给安岳捐书。到目前为止,前后应该已捐赠了接近1万件实物,总重量达4吨。”汪毅如是说。
当这些陪伴自己半生的资料物品进入安岳县图书馆时,他的眼中既有不舍,更有欣慰。如今,安岳图书馆内的“汪毅特藏馆”已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和旅游“打卡”点。
光阴流转,当年安岳县文化馆里陪伴过汪毅的一棵紫荆树苗如今已亭亭如盖,汪毅对安岳石刻的研究,也如同年轮一般,层层叠加,愈发厚重。这位文化守望者用一生兑现了对安岳的承诺,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故事,也因他的执着守护而得以更好地传承。
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


